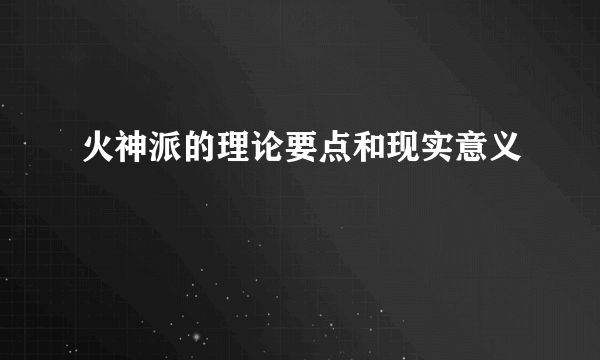
主讲人:张存悌
一、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是火神派最基本的学术观点。“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突出阴阳作为总纲的地位,这就是郑氏临床辨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由此,临床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套用一句《内经》的话说,就是“谨熟阴阳,无与众谋”。“病有千端,漫云易为窥测,苟能识得阴阳两字,而万变万化之机,亦可由此而推也。”“学者苟能于阴阳上探求至理,便可入仲景之门也。”本人体会,艰苦摸索二十余年,于今方有登堂入室之感,上了“一个境界”,明白了阴阳至理,才真正会看病了,这是学习火神派的首要收获,其意义不下于掌握附子的运用方法。“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我们以“舌脉神色口气便”七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舌——舌青滑或淡白,满口津液;脉——脉息无神,浮空或细微无力;神——其人安静,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色——面色唇口淡白;口气——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便——二便自利。这样应该更清晰,便于掌握了。这些,郑氏通常又称为“阴象”、“阴色”、“阳虚实据”。“阴虚辨诀”则与之相反。其中郑氏将舌象列在首位,强调舌的认证价值,是其独到之处,许多医家往往单凭一个舌象就能作出阴证的判断。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上述通常按照湿热、阴虚、阳亢、实热等来认识的病变,用这两把尺子衡量,不难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从而用扶阳法治疗取得可靠疗效,这对目前严重的中医西化倾向,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也是学习火神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敢用附子。卢崇汉教授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做中医的始终要跟着脉证走,不要跟着指标走。”陈修园有一句名言:“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己;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己。”可见辨清阴阳的重要意义。
二、重视阳气,擅用附子,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
1.阳主阴从,重视肾阳火神派理论上推重阳气,对姜附等温阳药物的应用独树一帜,积累了十分独特而丰富的经验,这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本人将其归纳为两句通俗的话:万物生长靠太阳,百药之长数附子。广义上讲,一个医家如果推重阳气,广泛应用附子,就可以归之于火神派,当然这是相对于经典火神派而言。郑钦安重视阳气,有2个特点:其一是阳主阴从;其二是独重肾阳。“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下焦肾阳是上焦中焦阳气之根。也就是说,在诸种阳气中,郑钦安又特别强调肾阳的作用,“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
2.擅用附子,独树一帜恽铁樵说:“附子最有用,亦最难用。”事实上,药之本性在毒,无毒则不成药。李可老师认为:“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近代医家杨华亭指出:“乌头虽毒极,而入药主治之功能,则为诸药所莫及。”“惟能用毒药,方为良医。”近代浙江名医范文甫先生有一句名言,“不杀人不足为名医”,意谓不善用峻烈药(峻烈到能杀人)者,难以成为名医。因此,是否善于运用毒药、峻药,最大限度的发挥附子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名医的重要标准,对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尤具现实意义。祝味菊甚至说:“变更附子的毒性,发挥附子的特长,医之能事毕矣”。是说医生的全部本事就在于擅用附子,可见熟练应用附子的意义多么重要。许多人攻击火神派滥用附子,恐怕与他们不敢用附子有关系。
1)专用附子,不夹阴药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今人亦有知得此方(指四逆汤)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针见血。运用附子单刀直入,不夹阴药,这是火神派十分重要的观点,这就无怪乎火神派应用最多的方剂是四逆汤了。许多医家在用附子时经常夹以人参、熟地、白术等药,恐怕就没弄明白这一点。
2)熟知附子的用药反应“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吃一二口冷水,皆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五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切不可为这些反应所迷惑而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入歧途。初用附子者,必须要过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会用附子。郑钦安关于服用附子的反应鼓励我们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
三、详辨阴火,精深独到,是火神派最精华的部分。单纯的阴证辨认并不难,“阳虚辨诀”指示得非常明确。重要的是,郑氏对阴寒偏盛所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所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他称之为“阴火”者,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所谓“阴火”即阴证所生之火(与东垣之阴火不同),又称假火,本质是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种种“肿痛火形”其实是假象,常见的如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颧红、目赤、耳鸣以及内伤发热、皮肤包块红斑、足心发热如焚等都是极为常见的病症,看似火热之象,其实是真寒假热亦即阴火,极易被误认作火症和阴虚火旺,俗医治以滋阴泻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头面五官多阴火”,俗话所谓“上火”者,除上述常见者外,还有目胀、耳胀、鼻燥如冒火、口臭、口苦等,真是五花八门,郑钦安有一句名言:“总之众人皆云是火,我不敢即云是火。”就是说的阴火,差不多有“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他用大量篇幅阐明阴火的假象与本质,勘破阴霾,指点迷津,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充满真知灼见,因此我称之为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唐步祺先生说:“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即指阴火辨识而言。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阴火、假热证的辨认上,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今天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敬云樵先生最有见识的第二条批注就是:“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粗工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
四、阴盛阳衰的病势观所谓病势观,是指医家对群体社会的发病特点和大体趋势的概括认识,它是关系到医家和学派的学术特点和认识疾病的前提,一般与社会、时代及地域、气候特点密切相关。郑钦安说过:“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是说俗医“喜清凉而恶辛温”,滥用寒凉伤阳,导致世人“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指出阴证、寒证占了大多数(盛),而阳证、热证则少见(衰)。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郑钦安关于“阴盛阳衰”的病势观,仍然是适用的,这正是火神派重视扶阳、擅用附子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传承、弘扬火神派的缘由所在。祝味菊说:“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已故河南名医周连三(1889~1969)说:“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卢崇汉教授说:“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我的用方可以说99%的都是纯辛温药物组成的。”他甚至说到:“末世的很多医者确实搞不清阴阳寒热了,那怎么办呢?就去守这个‘法宝’吧。开个玩笑,如果你能守好这个‘法宝’,就是乱打也会打中百分之七十。换句话说,你乱打都会变成中工,因为十愈六七就算中工”(《扶阳讲记》)。他所称的“法宝”指的是陈修园那句话——“宁事温补,勿事寒凉”。李可先生说:“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本人体会,临床上确实“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
五、用药的经方法度火神派根源于伤寒派,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风格,用方大都是经方,药味少,药量重,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二三味,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法度甚严,达到郑钦安所称“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即郑氏用药的鲜明风格,具有这一用药风格者,本人称之为“经典火神派”。分经典火神派、广义火神派完全是出于研究的需要,绝非要分出高低,不是说经典火神派就比广义火神派高明,广义火神派就不如经典火神派。事实上,广义火神派恰恰丰富和发展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开拓了用药思路,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李可先生脾肾并重的观点、补晓岚先生温辛并重的“补一大汤药”,以及在座诸位(包括许多未能发言者)的独特经验等,都推动了火神派的学术发展,让这一学派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有关争议的两点说明其一.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李中梓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