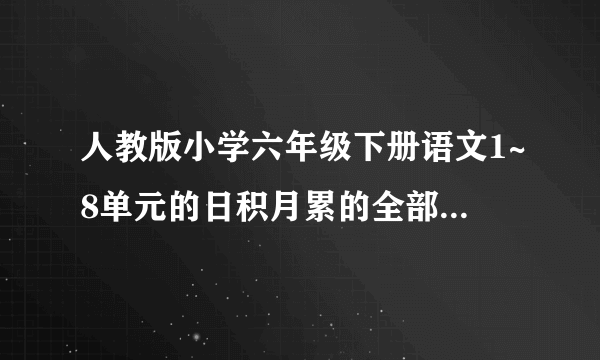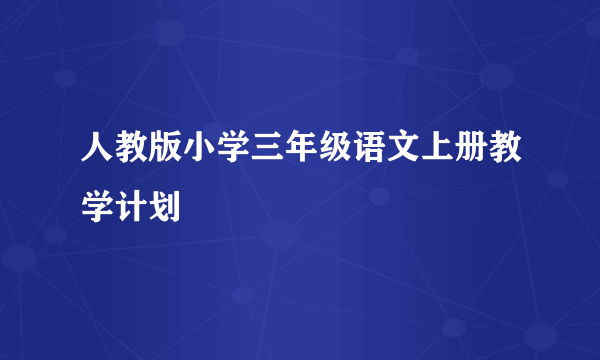也说“木叶”
安徽大学中文系李睿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一文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成为第5册(必修)的一篇课文。林先生此文使笔者深受启迪,获益匪浅,但细细读之,感到文章中有些观点,似乎还不甚稳妥,需要推证商酌。
文章开头引用屈原《九歌》的名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举例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接着运用举例比较的方法,进一步说明诗人们通过“木叶”写出为人传诵的名句,而“树叶”很少被采用。
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宇:“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那就是:“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而“树”是具有繁茂技叶的。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所暗示的颜色。那就是:“树”使人想到“褐绿色”的树干,而“木”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榄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木”是象形字,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树”是形声字,人们看到它,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木板”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栓、棍子、梳杆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何况树干的颜色,也不都是“绿色”的。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李白的《梁园吟》写道:“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其中的“木”就是写夏季高大茂盛的树。王维的《辛夷坞》一诗有“木末芙蓉花”的句子,写的是春天盛开的芙蓉花,它用的是“木末”而不是“树末”。还有杜甫有名的诗句“城春草木深”(《春望》)及韦应物的“春深草木稠”(《游灵岩寺》),写的都是春天长势挺拔、生机盎然的树,但都未用“树”而用“木”。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瓢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马戴的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濡上秋居》),尤为脸炙人口,但用的也是“树”。
本文上面所举的例子,都说明“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王绩的《野望》诗分明写道:“树树皆秋色”,连用两个“树”字,强调的就是秋天无生机的萧索的树,而此处如改为“木木”则断然不可。再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得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再比如“古木”一词,古人用得也多,但可以是秋天的树,如“古木呜寒鸟”(魏征《述怀》);也可以是春夏的树,比如“古木生云际”(陈子昂《白帝城怀古》);至于“古木无人径”(王维《过香积寺》)和“深山古木平”(陈子昂《晚次乐乡县》,人们不大容易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季节的树,而且也无须弄清楚了。我们还是像李白的“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的好,只把“木”当做一般意义上的树,而不必深究是什么样的树了。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首先,“木”“落”“叶”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再次,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较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昧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