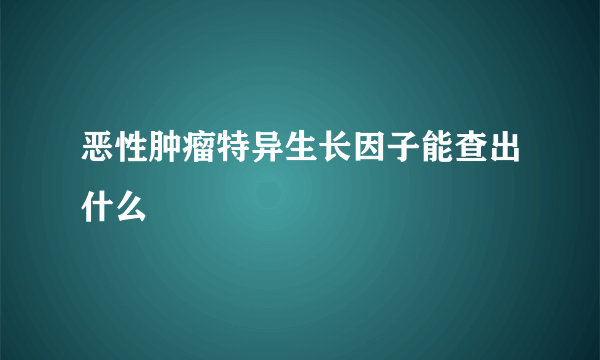一九九五年十月被告人朱昱伙同其在X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李某一起来到北京医科大学解剖系。冒充是X美院学生(当时被告人朱昱已从X美术学院附中毕业,而且并没有继续上美院)。以参观学习为借口,对尸体标本进行拍照并购买医用标本模型。 一九九七年五月被告人朱昱又一次来到北京医科大学解剖系。这次他仍然冒充是美院学生。当被告人朱昱正准备租借该系的医用标本时,恰遇一位与美院曾有过联系的北京医科大学解剖系老师,被告人朱昱怕谎言被揭穿,便只好形色匆匆地离开了。
此后,被告人朱昱并没有对自己利用尸体进行所谓“艺术创作”的计划死心,他又于一九九八年四月来到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解剖系,找到该系的老师王某。被告人朱昱吸取了上次在北京医科大学解剖系的经验,这次他没有再冒充是美院的学生或老师,而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去找该系的老师。但为了不引起别人的不信任,被告人朱昱还是含糊地说自己与美院的某个艺术研究机构有关系。
当被告人朱昱发现他所说的一切并没有被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解剖系的老师怀疑后,他便多次来到该校,不断地用他是在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的态度与该系老师交流,以达到获得其最终信任的目的。
一九九八年十月被告人朱昱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便提出向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解剖系借用尸体标本的要求。该系老师这时已完全相信被告人朱昱是在进行“艺术创作”。但考虑到被告人朱昱所借用的尸体标本可能会有损坏,便提出:如果被告人朱昱能保证所用的尸体标本完好无损,便可同意其借用。但如果尸体标本在朱昱进行“创作”时有损坏或不能归还该学校,便只能以租借或出售的形式给予其使用。
被告人朱昱欣然接受了这一条件。并要求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解剖系的解剖室进行他的搅人脑的行为,即所谓《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作品。
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二时,被告人朱昱利用学校放假人少的机会来到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解剖系。用事先从该系购买的人脑标本五个,在该系的第二解剖室教室进行了所谓“艺术创作”。他将五个人脑标本切割、搅碎,并将搅碎后的人脑标本用福尔马林浸泡,灌装到八十个玻璃瓶中。
事后,被告人朱昱将这八十瓶人脑罐头贴上商品标签。在标签上写明了是“脑浆”,还标明了产地、生产日期、储藏方法等产品所需的要素。在瓶盖上则贴有人脑制品“禁食”的字样。
在朱昱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他的搅脑浆(即所谓《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作品)之后,利用人的尸体进行所谓 “艺术创作”的丑陋现象就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圈中蔚然成风。给健康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
一九九九年四月被告人朱昱将
当时上海媒体这样报道被告人朱昱的这个所谓“艺术作品”。《新民周刊》称:“但不少人对这件‘作品’不敢直视,记者观察到,没有一个人在电视机前看完记录脑浆制作过程的录像片。‘太可怕了’,‘太恶心了’,‘没有必要这幺做’,不少观众向记者表达了这种感受。”《新民晚报》称:“进门处的‘超市’货架上陈列着一瓶瓶标明‘脑浆’的糊状物,注释是‘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给人的直观是毛骨悚然。”
被告人朱昱在完成了他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关于脑浆的制作过程之后不久,又于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在北京朝阳区芍药居小区202号居民楼地下室举办的《后感性》展览中完成他的所谓“艺术作品”《袖珍神学》。他在该“作品”中将尸体的上肢标本悬挂在天花板上。